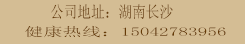![]() 当前位置: 知了 > 知了的繁衍 > 汶川,属于我的记忆碎片
当前位置: 知了 > 知了的繁衍 > 汶川,属于我的记忆碎片

![]() 当前位置: 知了 > 知了的繁衍 > 汶川,属于我的记忆碎片
当前位置: 知了 > 知了的繁衍 > 汶川,属于我的记忆碎片
十年了,是否要整理一下,关于汶川的那些记忆碎片?
1
年5月13日,北京
地震,不可抗拒的战栗……
昨天下午同事来电话,说四川地震了,7.8级。不由得心头一震。网上的最新消息是: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2万,震中汶川仍有6万人杳无音信。
此刻几位同事已经在飞往灾区的飞机上,祝他们顺利到达,祝他们平安,祝他们早日发回报道……
今年不知怎么如此多灾多难。
在所有的自然灾害中,地震,是最让我恐惧的一种。
年唐山大地震后全国各地似乎都余震不断,连远在西北的我的老家宁夏,大家也都在忙着防震。夏夜,全村人都住在麦草搭成的小棚子里,或者将啤酒瓶倒立在桌子边沿报警以便随时逃命,大概是我幼年最早的记忆之一了。(很不幸我最最早的记忆是两起死人事件,其中还有一起是上吊自杀的。)那种恐慌不安的感觉似乎多年以后仍然能清清楚楚地触摸得到。
中学学地理时,惊讶地发现宁夏正处在地震带上,狭小的“领土”几乎与地震带完全重合。小规模的地震时有发生,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有两次——
一次是正吃晚饭,突然感觉脚底晃动,妈妈一把拉开了厨房门,爸爸拎起正在吃饭的妹妹一步就蹿到院子里去了……
还有一次,已经放学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还在教室里。突然地震了,我的座位在最后一排(上初中的时候我还属于高个儿,后来就不长了,唉),紧挨着后门,我也是嗖一下就蹿出去了。在院子里站了好半天,犹豫要不要回教室去拿书包……
开始留心有关地震的各种说法。看到“小震不断,能量逐步释放,就不会发生大地震”,心下大喜;转眼看到“小震不断是大震的前兆”,又转喜为忧。
每一次地震,都能感觉到那种不可抗拒的战栗从地底传至脚心,传至内心深处,再传遍全身。
上大学了,北京似乎比较平静。但是有一年放假回家,在火车上经历了我迄今为止最恐怖的阅读体验——看了一篇关于年海原大地震的报告文学。那次大地震有8.5级(后来据说还不止),震中烈度12度,震波绕地球两圈半,余震持续3年,(在地广人稀的西海固地区)死亡23万多人,方圆2万多平方公里地带几乎成为无人区。据那篇文章描写,当时的情形用“天崩地裂鬼哭神嚎”来形容一点儿都不为过——大地确实裂开了长若干米、宽若干米的许多口子,而且一张一合,霎那间就不知吞噬了多少条生命。最惨绝人寰的一幕,是一对老夫妇拼尽全力打开门,将自己的女儿推出去,却怎么也没想到门外恰是一条裂缝,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落入地狱之门!
此后,无论远近,无论大小,地震的消息总是会令我不寒而栗。我有幸从来亲身经历过大地震,却会偶尔在梦中看到似乎是地震后的惨状,并且被那种极度惶恐的气氛所包围。
水灾,风灾,火灾,冰雪灾害……可怜的人,已经承受了这么多,还要面对这来自深不可测的地底的振颤与撕裂带来的毁灭性打击!
但愿,但愿那6万人安然无恙……
2
5月19日深夜-20日凌晨,成都
下马威·倦极而眠的记者……
人民画报社记者陈建和段崴,从5月13日赶赴灾区,到5月19日我们这一拨人去与他们会合时,已经在灾区奔波了整整7天。
那一周,留在后方的编辑们也拼尽了全力:守着时断时续的微弱信号与前方联系,一边流泪一边写稿、找图、排版,三四天里几乎不眠不休,终于提前完成了第六期杂志——抗震救灾特刊的编辑制作。
5月18日杂志付印当晚,我刚进家门,又接到通知:我被列入第二批赴灾区采访团名单,须即刻到局里开行前会,次日出发。
第二天,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就睡着了,直到“咣当”一下飞机落地,我才惊醒过来。带队的领导说,还从来没见过这么能睡的人。
当晚四川电视台滚动播出有6至7级余震,让大家注意防范。但我们几拨会师的记者正在宾馆餐厅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没看见电视。
11点左右,一扭脸发现整个餐厅都空了。
开始还很镇定,先来的人,像陈建、段崴他们,也都说没事,可是餐厅服务员再三来警告我们有余震,而且说他们要下班了,我们只好散会。
出了餐厅,只见同住一个宾馆的某国救援队队员全副武装、携带着各种先进救援设备开出了宾馆,在外面离大门最远、靠马路最近的路边树下围成一圈坐下了。
宾馆在成都南门附近,临近午夜,但见大街上车水马龙,有车的成都人正纷纷赶往城外开阔地带,没车的市民也走出家门,搭帐篷、蚊帐甚至露宿街头……
好一个下马威!
我们也只得收拾“细软”,到外面备震。
新来乍到,我们还能站着坐着,可陈建、段崴屁股一挨地就躺下了。
好像睡得还挺香!
希望两大帅哥儿不会怪我“发表”他们“正面全裸”(引用段崴原话)的照片——其实哪有全裸?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他们的正面,永远都有抱在怀里的相机。
3
5月20日,汉旺镇
比死亡还深的寂静
下面,是人民画报记者陈建目睹的救援现场——
5月15日上午,小雨,绵竹市汉旺镇东汽中学。我相信,这里,魔鬼一定来过。五层的教学楼只有两侧的楼板依靠救援的缆绳站立着。中间的水泥楼板东倒西歪地交错着,在交错的缝隙中,孩子们小小的身躯蜷缩着,很多,都已经冰凉。在二三楼之间的楼道里,半倚着一个穿红白相间运动服的女生。她是杨柳,东汽中学高二的女学生,她的双腿,被一根水泥柱重重地压着,她的身边还有一具同学的遗体也被紧紧地压着,不能移动。60多个小时。我无法想象,在5月12日那个大雨滂沱漆黑冰冷晚上,她是怎样度过的。但我相信,她心中一定有着非常强大的力量——她不时地向与她咫尺天涯的人们虚弱地挥手,告诉他们,她还活着,她要活着。倒塌的教学楼前,是一条刺目的黄色的警戒线。警戒线的前面,是一条五米宽的小河,河的对岸,是黑压压的人群,杨柳的爸爸妈妈就在人群里,他们没哭,只是静默着,一直望着女儿的方向。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中国国际救援队的现场指挥告诉我,现在只有两个方案,一是给杨柳罩上一个笼子,防止在吊起那根压在她腿上的水泥柱时再次引发的坍塌危及杨柳的生命,但让他们更担心的是,这样很有可能会让废墟里其他幸存的孩子失去生命;另一个方案是——截肢,把这个孩子的双腿留给这片废墟。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救援人群中有一些小小的骚动。紧急救护的医护人员围成一个小小的圈,我冲过去,看见的是医生眼中的泪,还有一把缠着纱布的钢锯。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这也是孩子自己的决定。……
5月20日,当我们站在这片废墟前的时候,已经看不见被困的孩子,看不见心急如焚的家长,看不见救援人员,只有面前这片危楼——“好像吹口气就能把它吹倒”(陈建语)。
没有风,没有鸟叫声,也没有哭声喊声,更没有了当日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嬉闹声。
一片死寂,甚至,是比死亡还深的寂静。
校门上挂着一只钟表,两旁写着“珍惜”二字。看了看表上的时间,竟然就是我们在那里的时刻,14时50多分。
时间还在继续,而那么多年少的生命已戛然而止……
4
5月20日,绵竹市灾民安置点
帐篷之间
5
5月21日,都江堰,聚源中学
灰白地带
那天没带相机,可能是因为有三位摄影记者同行的缘故。
面对着聚源中学这片废墟,呆呆站了一会儿,觉得非得拍点什么不可,于是拿出手机来拍。
用得不熟练。不知碰了哪个按键,画面突然变成一片红色,再按,再按,又依次变成绿色调、蓝色调、底片效果、黑白效果……
怎么正常的彩色效果不见了?拇指按下去,只看见或冷或暖或黑白各种色调的废墟在眼前闪过,我有点不知所措。
两三圈过后,定神仔细再看,才发现黑白效果之前出来的其实就是彩色效果。但那是怎样的彩色啊!残垣断柱,碎砖破板,胡乱地堆积在一起,画面中,只有深深浅浅的灰色——怪不得手机两三次切到彩色模式我都没有发现。
环顾这一片灰白地带——除了眼前灰白色的瓦砾堆,还有身后灰白色的操场:操场上的白色是石灰的颜色,5月12日之后的两天,操场是孩子们的临时停尸场——震惊,悲凉,到无可言说。
默默转到侧面,赫然发现有两片醒目的黑红色块,那是两片残墙上幸存的黑板以及黑板上的国旗。
国旗旁边,孩子们的两条座右铭各剩了半句:近处的写着“自信快乐”,远处的墙上是“无所畏”三个字。
自信快乐的孩子啊,无所畏惧的孩子啊,你们现在在哪里?看着这几个字,感觉心里被生生掏了几个洞一样,痛得无法形容。
就在“自信快乐”之下,有两个中年男人,一个站在废墟旁,神情忧郁;另一个面无表情,一会儿走上废墟,一会儿下来,若有所失。
站着的那个告诉旁边围观的几个人:他们两个人的儿子是同班同学,他们面前就是儿子原来所在班级的位置。地震后,他的儿子被救了出来,刚出来的时候还活着,过了一会儿就死了,而那个人的儿子一直都没有找到——那天,扒出一个孩子,他们所有的家长就追过去认——那个人的儿子始终没有出来……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稳,也没有哭;那个至今没有找到孩子的父亲听着,也仍然是眼中无泪,面无表情,只是恍恍惚惚一会儿上废墟,一会儿又下来。
10天!这位父亲,还有这些父亲,以及没在现场的母亲们,该是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才磨成今天的平静和恍惚?
6
5月22日,什邡市蓥华镇
面目全非
什邡市蓥华镇的一个化工企业——蓥峰实业,仍然耸立的只有这些柱子了。像是在无语问苍天,面目有点狰狞。
7
5月22日,什邡市灾民安置点
笑,如雨后的阳光
黄金渺(中)和毛芳苗(左)是同班同学,5月12日两点28分,她们刚刚解完手要去上课,突然感觉房子摇得很厉害。
她们跑到操场上去看究竟,还不晓得是地震了。
她们的同学,一共63个,差不多都遇难了,幸存者分散在各处,她们也不知道一共有多少。家里人因为都在田里忙农活而幸免于难。黄金渺一岁多的小表妹李思相怡(双胞胎之一)被家里人抱出来玩,也没事。
“刚才他想亲我妹妹呢!”5月22日下午5时23分,在什邡市灾民安置点,说到一个比妹妹大一个月的小男孩,她们笑了。
她们的笑,如雨后的阳光,令人倍感温暖。
8
5月23日,北川陈家坝乡
寻找赵海清
地震后第三天,电视里一个男人泪流满面的画面使无数人为之动容:他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儿子,妻子也下落不明。正在接受采访时,对讲机里传出呼叫他的声音,他立刻擦了把眼泪转身跑去抢险了。
通过各种渠道,我们得知他是北川县陈家坝乡党委书记,名叫赵海清。但连着几天打他手机,听到的总是“您所拨打的用户不在”,让人不由得一直悬着心。
陈家坝位于北川县城以北18公里的山坳中,地震之后,陈家坝到县城的公路打通了又堵住,通讯也是时断时续的。
5月23日,我们从成都出发,去探访陈家坝,寻找赵海清。
“能够在这儿坚持战斗到今天的,都是英雄!”
因为北川县已经封城,我们只能绕道江油市,从北边的桂溪乡南下陈家坝。盘山路两侧,不时能看到刚刚清理到路边的滚石滑土。
行路虽然难,但一进入陈家坝地界,想找赵书记就很容易了。在路边问一个老乡,他指指前面说,“在发救灾物资那儿”;到了发救灾物资的卡车旁再问,有人回身一指,“在那个篷篷那边”;转过帐篷一看,人很多,问哪个是赵书记,马上有人回答,就是戴眼镜那个。
赵书记身材敦敦实实的,鞋子与卷起的裤脚上都沾满尘土。一张脸晒得黢黑,额头面颊有不少地方爆了皮。戴一副和他的圆脸很相称的圆眼镜,显得有点书生气,甚至还有点稚气。
他站在那里,正捧着一个纸杯吃饭。但大大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长相忠厚和善的赵海清,在一边吃一边跟一个灾民吵架!
“才吃了一顿饭,连早饭都没吃上……”那个灾民大声嚷嚷着,赵海清也是一脸怒色。
但他正要去开一个协调会,没时间继续吵,也顾不上向我们解释眼前的情形。
乡村公路旁,满地都是麦秸。两条简易长凳上,大家落座:来自山东的省政府秘书长,云南的某部师长,内蒙古的卫生厅厅长,北川县的政协副主席,香港的老板,广东的医生,还有安徽蚌埠、河南鹤壁等地的各种救援力量,以各种口音的普通话和赵海清一起分析陈家坝的形势——县城上面的堰塞湖要泄洪,必须赶快疏散群众,而灾民正大量回迁,又急需安置;可能回来长住的灾民在左右,而全乡18个村里能够安置灾民的只有金鼓、红岩和双堰3个村,地方紧张先不说,帐篷食品,防疫防火,压力都很大。
“我们得保证现在活着的人安全啊!”赵海清说。大家纷纷点头称是,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出谋划策,比如建立烽火台式的接力观通站为堰塞湖报警,分散居住、集中做饭以避免火灾,帮助灾民抢运粮食、财产、家畜……
会还没开完,就有人把赵海清叫了起来,请他核实重建房屋、学校、医院的数量。然后一直有人围着他,有向他发号施令、需要他去办事的,也有向他请示、等着他发号施令的。各种事情交织在一起,难怪赵海清“每天都睡得很少,感觉脑袋不够用”。
还有灾民七嘴八舌地在旁议论:“住在帐篷里的老人孩子,到夏天这么热,中暑了怎么办?”“土地不够嘛,现在一个人发斤,斤,那明年呢?后年呢?”“迁出去,现在地都是包给私人的,没法安置嘛!”……
“山东省来对口支援我们,给我们建简易平板房,不让我们的灾民一直住在帐篷里,”赵书记发话了,“平整土地,咱们老百姓得自己出力哟!”
“这个书记很不简单!你看已经10多天了,把这个灾区整得井井有条。”北川县里来的一位干部仿佛不吐不快:“能够在这儿坚持战斗到今天的,都是英雄!”
“他们的在天之灵应该能理解我”
“他从12号到今天就一直守在这个地方。”一位姓张的乡干部主动告诉我们,“他的家人都在曲山镇,就是北川县城。老人孩子遇难了,他爱人埋在倒塌的房屋里,受了重伤,第二天下午才被救了出来,转移到重庆去治疗。”
人群稍稍散去,赵海清的眼泪慢慢地涌上来:“我侄女也遇难了。我家就我和弟弟两弟兄,孩子都上幼儿园。幼儿园在山边,山体滑坡把他们都掩埋了。”他的泪水夺眶而出,“现在只要是北川人,可能没有几个家庭是完整的了。”
“非常思念他们。真的,非常想……”喧闹的双堰村仿佛突然静了下来,天地间只留下这个嘶哑低沉的声音:“前天晚上吧,我在老乡那里买了些香和纸,就在桥头那儿,对着北川方向,烧了纸,烧了香,给父母磕个头,做了个检讨。”
泪水扑簌簌地随着他的话音滚落,“确实,我到现在都没去找他们!爱人在重庆住院,我也没去看她,老丈人还在怪我,说你就知道工作工作……”
刚刚那个指挥若定的赵书记不见了,眼前只有一个伤心的儿子,悲痛的父亲,愧疚的丈夫——他没有放声恸哭,也没有泣不成声,但这样的黯然垂泪,更让人无言以对。
旁边有人插话,打破了短暂的静默:“有人不理解,说你没有人性还是怎么的。什么人性?这里离不开,没办法!人心都是肉长的,谁不疼自己的孩子,不恋自己的父母?”
“我现在这样子,他们的在天之灵应该能理解我,不会怪我的。”赵海清双手捂住脸向外一抹,像洗了把脸似的,擦去了泪水。
我们很想深入他的内心世界去一探究竟:面对这毁灭性的灾难,自己的家庭也遭受如此重创,他怎么还能坚守岗位?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在支撑着他?
这个问题,像是在堰塞湖的堤坝上打开了一个口子,使赵海清堵在心里的话汩汩滔滔地涌了出来——
“作为一个干部,我有我的职责。我是这儿的书记,这里需要我。因为有他们这些人,我才是书记;没有他们这些人,也就没有我这个书记了。他们也和我一样有兄弟姊妹,他们也一样是我的父母。在这么大的灾难中,可以尽我最大的努力为大家做点事,我能够感到我的价值所在。
“还有,我在这儿,也就能把我这支队伍带起来,向我看齐。我都没走,你们谁走?我们乡长的父亲、妹妹妹夫、弟媳妇都遇难了,乡干部直系亲属有14人遇难。每人只给一天假,出去报报平安,看看在世的家人,然后必须回来工作,因为你是干部。你想一下,多人,没有干部行吗?
“你刚来的时候看到我在跟一个老百姓吵,我是在批评他。他在和我们一个乡干部吵架——那是退下来的老领导杨主席,50多岁了,爱人受了重伤,唯一的女儿,刚刚参加工作,也遇难了。你刚才不是也说,我们还年轻嘛,可能今后还可以生儿育女,但他们,一辈子的努力,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希望,就都没有了。他负责发放食品,那个老百姓今天刚从城里的安置点回来,吵吵没吃上早饭什么的,杨主席说了他几句,他就要动手打人,我是不客气了——打人坚决不行!
“这几天县上下来的人很多,问起他们来,每个人都有很多亲人没了,你看他们也都在工作。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北川人,是大禹故里人,尽管损失很惨重,但是这10多天来,我还没看见几个人被摧垮,大家的肩膀都还能够扛得住!”
“是党员干部的站出来!”
不忍心再去追问任何人5月12日那天你在哪里,在做什么。但是,总还是能听到只言片语提起悲剧降临那一刻的情景。把这些片断拼接起来,我们就分明看见了赵海清和他的同事们在顷刻间变成一片废墟的陈家坝奔走的身影。
开始是有点响声,然后房子有一点晃动。地震了!他们赶紧跑出乡政府的办公楼。外面一片浓烟,就在他们前面不远处,“整个一匹山滑了下来”。身后,轰的一声,乡政府的一楼塌了,二楼“坐”下来变成了一楼。
一到安全地带,赵海清就立刻把全乡干部召集起来——除了一人遇难,剩下的都在。他们分了几个小组,分别负责紧急救人,医疗救护,疏散转移,后勤保障,治安维护。首先是寻找、抢救被埋到的活人。幸运的是,学校没有倒塌,中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从学校里疏散出来,乡干部又带着他们转移到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
当晚,废墟中,暴雨下,喊声哭声一片。赵海清对着人群喊话:“我们干部在,青壮年在,党员在!是党员干部的站出来!”灾民的情绪一下子就稳定下来。干部们从摇摇欲坠的商店里抢出一些粮食和水,分发给老人和孩子,而他们自己则是24小时没合眼,没吃一口东西。
第二天,他们从收音机微弱的信号中得知震中在汶川、北川县城的方向,就开始把群众向相反的方向——桂溪、江油一带转移,并且强行命令学校师生全部步行撤离。天下着雨,余震不断,山上还不时有石头滚落,但陈家坝小学近名师生在地震和转移中无一伤亡。
一边转移疏散群众,他们一边抢修通了陈家坝至江油的公路,又从乡政府院里勉强开出一台车,要将受伤的人送出去救治。当时很多人争先恐后地挤到车上,想坐车跑出去。赵海清下令:“先救伤员,你们不出来就不开车!”总算控制住了局面。到13号晚上,伤员就基本上都被送了出去。
到了14号,仍然联系不上县城,孤立无援,赵海清决定到绵阳去,报灾,求救。恰好那天他穿了一件警服——晚上太冷了,派出所没倒,他就从里面找了件衣服穿上了。那件衣服又瘦又小,他穿着连扣子都扣不拢。人又很脏,耳朵里面都是泥。到绵阳市政府门口,有人拦住问他:“你这个警察怎么这个形象啊?”他说了句“我是来报灾的”,就闯了进去。通过共青团绵阳市委,他总算找到四军医大的医生,搬了救兵进来。
就是那一天,车行至江油,手机有了信号,他接到电话,得知了父母妻儿的消息。
5月23日下午两点半左右,我们与赵海清握别,谁都没有注意到那是一个特殊的时刻。他矮矮胖胖的身影,随即消失在人群之中。
关于他,除了看到的,听到的,我们所知并不太多,却已足够让我们记住他——
赵海清,羌族,年3月生于北川,在县城长大。出生时算命先生说他名里缺水,因此父母给他起了这个名字。
他的经历,可以说相当平顺:年纪轻轻的,他已经当了6年多乡镇领导——陈家坝3年书记,桂溪乡3年多乡长。到桂溪当乡长之前他在团县委工作了6年,而在那之前,他是一位老师,就在桂溪中学教书——绵阳师专毕业,教师是他的本行。
“欣赏别人是我最大的爱好。”赵海清说。因此,他很尊重乡里那些老同志,老同志们也非常支持他,“从来没跟他扯过筋”,总是他安排了工作大家就高高兴兴去做。
也因此,他交友不少,闲暇时最喜欢和朋友聚一聚,玩一玩。可是现在,手机上保存的许多朋友的电话打不通了,他慨叹道:“以前的很多快乐已经不可能再有了!”
等陈家坝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正规一点了,他就要休假,去陪爱人散散心。赵海清说,“今后,家人,朋友,我都会更加珍惜。”
9
5月23日,北川
堰塞湖·烽火台
5月23日,绕道江油去北川县陈家坝乡采访。
车过了江油,就钻进山里。盘山路的一侧是陡峭的山坡,另一侧就是深深的山谷。一道一道滑坡的山体将青翠的峰峦撕开,远看像是土黄色的瀑布直落山脚。不时看见路的两侧堆着颜色新鲜的泥土和石块,显然是不久前刚刚清理到路边的。车行至桂溪,甚至看见对岸有半面山整个滑下来,在山谷中堆积成堤坝,堤坝之上那一潭碧水,就是在5·12之后声名鹊起的堰塞湖了。
听听灾民怎么说:
我们有一个水池子得米深。两个山碰过去,挤一块了,水就堵里面了。(就是堰塞湖?)我们有好几个在里面。一到雨季怎么办,洪灾来了怎么办?
再听听一直在陈家坝抗震救灾的云南某部师长怎么说:
肯定要决堤!北川县城救援人员已经全部撤出了。上面的堰塞湖储水量有1万亿立方,水深是70米,如果水出来,会对一个50到万人口的中等城市进行毁灭性淹没。老百姓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你讲1万亿立方他也没有概念。我们是在上游的分叉,主河道从上面下来有一个回旋,要拐一个度的弯,我们虽然是次河道,在上游,但是我们(和上游主河道)是一条直线。回旋的那个洼地最多也就两三个篮球场那么大,水流这么急,流量又很大,单靠这么小的回旋地肯定不够,水肯定要朝我们这个方向来,我们刚好还是直航道。所以我们打算建立一个接力观通哨,单靠一个观通哨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和护林队、矿山、武装部的同志一起,在几个点上设立几个观察哨,随时观察河面的情形,包括看水的流量、流速。接力只能通过简易的方式,因为现在通讯工具很匮乏,效果也有限,我们打算采取竖红旗、摇红旗的方式——第一个观察哨发现有情况,就摇动红旗,第二个观通哨发现以后也采取同样的方式报警。这就是针对堰塞湖的报警机制。
我在一旁听着,心中暗想:
简单点说,就是烽火台,对不对?只不过是红旗替代了烟火。
最古老的方式,却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10
5月25日,成都
6.4级的余震
回到房间,心仍旧狠狠地跳个不住。看看桌上的电脑,16点40。
刚才,大概是25分左右,突然感觉桌椅晃动——余震来了!
站起身来,看到床上一个小包的带子在微微颤动,同时听到沙发上的塑料袋悉悉索索作响。
冲过去打开门,听到住在对门、隔壁的同事都已经起身在说“余震”“余震”。又发觉头顶四周嘎啦嘎啦的,那是门框和楼板发出的声音了,虽然轻,但很清晰。
返身回到房间,正想趴在两个床之间的空隙里躲避一下,就听到领导喊:“快跑!”
于是抓起床上的小包,拔出门卡,带上门,往外跑。穿着宾馆里薄薄的拖鞋,脚底下很不利落,但是终于也跑到楼下,跑出大门,跑到路边树下的安全地带了!
气喘吁吁,心狂跳不止。
唔,来了一个星期了,不给你一次强烈的余震,岂不是不够意思?
在楼下呆了一会儿,看看一起跑出来的人陆陆续续回楼,我们也就跟着回来了。
网上已经有了消息:16时24分,青川一带发生6.4级余震。余震持续了一分多钟,成都有明显持续震感,绵阳亦震感强烈,人们很快从建筑物中跑出。
6.4级,够意思了!但现在,只能叫做余震。
11
5月20日,北京
泪水,总在不经意间滑落……
昨天,路过一间美发店,突然想弄弄头发。走进去,就把留了20年的长发剪了。
美发师一再问我:“我可剪了?你想好了?我可真剪了?你不觉得可惜?……”
我说:“没事,你剪吧。”语气无比平静——看着大把大把的头发从美发师手中落下,心里也是出奇地平静:头发嘛,剪短了还可以再长长!
但眼中泪水就要涌出来。不是心疼留了那么久的长发,而是,不知为什么,回来这几天,眼泪动不动就会冒出来。
在四川8天,我只流过一次眼泪,尽管很多时候面对着废墟也会心里发紧鼻头发酸,但真正流下眼泪只有一次。大多数时候,我都很镇定。
周三那天,单位中层干部会上,社长让我讲讲在灾区的见闻。讲到什邡的一条山沟如何被夷平,讲到聚源中学一栋教学楼如何塌得不成样子,讲到东汽中学一面墙上全是大叉子的楼如何触目惊心……都还没事。本来接着要说山体滑坡的情景,刚说出“那些山……”,突然声音哽住,眼泪哗一下就流了出来,再也说不下去了。
开完会去技术中心还移动网卡,一张口眼泪又流下来,话也说不清楚了。
好像原本密封的泪腺突然打开了,这几天,经常是说着说着话就泣不成声,有时候,说的话题跟地震丝毫没有关联。
而且,似乎是时差没有倒过来,人整天都有点恍惚。
今天以短发的新形象示人,每一个同事,不管男女老少,都是很吃惊的样子。
看来变化的确很大。变了的不仅仅是发型,也许,还有神情,还有心态……
12
8月5日,北京
关于地震,已不知从何说起……
朋友来短信,说前两天看了我的博客,才知道我去了地震灾区。
她问,肯定对你影响很大吧?
影响大吗?我不知道。现在,关于地震,我已经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其实当初刚从灾区回来的时候,就有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如果要说看得全面,看得真切,看得惊心动魄,其实在北京看电视可能更有优势。但是毕竟去了一趟,亲眼看了,这件事就变得有点personal(一个英国朋友的用词)了。也许正因为有点personal了,反而更不容易对他人说得清楚。
下面是我从四川回来后大概两周的时候写给前面提到的那位英国朋友的一封信,讲的是我在5·12后一个月内的经历和当时的心情——半瓶子醋的英语,可能有不少语法问题,但内容却是真切无误的。
IhaventbeenlivinganormallifesinceMonday,12May,whenthedevastatingearthquakehitChinasuddenly.WeweresummonedtoanurgentmeetingbyadirectorofCIPGthatnighttodiscusswhichjournalistsshouldbedispatchedtodisasterareasandhowtheywouldgothere–transportationand
转载请注明:http://www.zhiliaoa.com/cxzz/106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