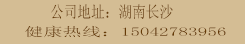![]() 当前位置: 知了 > 知了的生活环境 > 成年人处世潜规则请收起你的ldquo
当前位置: 知了 > 知了的生活环境 > 成年人处世潜规则请收起你的ldquo

![]() 当前位置: 知了 > 知了的生活环境 > 成年人处世潜规则请收起你的ldquo
当前位置: 知了 > 知了的生活环境 > 成年人处世潜规则请收起你的ldquo
文
摆渡人,来源
摆渡人(ID:baiduren66)
我们小区有两家超市,位置差不多。
经营第一家超市的,是一家三口。
他们家服务挺差,或者干脆可以说没有服务。
不管你什么时候进门,他们超市都保证没人搭理你。
想买什么东西,自己找,找好了自己装。
守在柜台跟前的,有时是他们胖嘟嘟的儿子。
那小子一边打游戏,一边不耐烦地给你结账,连正眼都不会瞧你一下。
不过这还算好,他爹比儿子还不靠谱,如果换他来守柜台,那就更糟糕啦。
他记不清东西的价格,每拿起一样东西,就要大声问老婆:“这个多少钱?”
她老婆穿着一件不男不女的短裤,正坐在马扎上削菠萝,远远地瞥一眼,报价。
经营第二家超市的,是个挺精神的小伙子。
小伙子刚来没多久,创业劲头很足,嘴巴又甜,说话像讲相声,不管是大妈大婶,还是爱脸红的小姑娘,都能被他逗得咯咯笑。
他一天到晚守着柜台,只要有人进店,他不管在做什么,都会立马起身,说声:“你好。”
结账的时候,小伙子也很大方,所有零头都不要,顺带来个半鞠躬,说句:“下回您再来!”
所以小伙子的店一开张,我就在心里嘀咕:“那一家三口的店恐怕要黄。”
没想到,几个月过去。
一家三口照旧爱答不理的样子,生意却一点没少。
反倒是小伙子的店,渐渐冷落下来。
原来,这个小伙子因为没经验,找的货源很差。
同样是芒果,隔壁超市是甜的,他家却是酸的。
同样是鸡蛋,隔壁超市个个新鲜,他家却已经散黄。
没有人会为了几句甜言蜜语,就去买酸掉牙的芒果,和散黄的鸡蛋。
就像没人会因为你是个好人,就容忍你一次又一次的失误。
很多人相信,做人比做事重要。
其实不对的。
你做人怎么样,是你自己的事。
而你做事怎么样,才会直接关系到我的利益。
我认识一个原料供应商,很会做人。
不管天南地北哪里的客户来探访,他都会亲自作陪,车接车送,好酒好菜地招呼。
第一次见他的人,没有一个不会竖起大拇指:“这人够义气!这个朋友值得交!”
可最后,这些客户几乎都跑光了。
因为这个供应商,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经常违约。
明明说好第二天能送到的货,却在当天早上打“哎呀,抱歉抱歉,这批货没赶出来,兄弟多包涵!”
一次两次还可以,次数多了,谁能天天停下流水线等他?
有客户好心劝告:“你别整天到处招待,有那时间,去厂子里转转,赶赶进度好不好?”
可他坚持认为,只要把客户交际做好,订单就会源源不断地飞来。
就这样,没两年,他的厂子垮了。
这个人经常喝闷酒,感慨:“世态炎凉啊。”
在他看来,他对客户很够义气,可是客户却不念恩情,连宽限几天都不肯。
而实际上,他对客户的义气,对人家来说,不过是小恩小惠。
用小恩小惠,来挑战对方的原则,自然会输得很惨。
你一定听过一个词,叫“恃才放旷”。
一般被这个词形容的人,都有一些共同特点。
比如,在某个领域特别专长,业务做得特别漂亮,但不善交际,讨厌应酬,对人冷冷淡淡,更不会说什么漂亮话。
可能有人觉得可惜。
你看,他做事都做得那么好了,如果再学会做人,那该多完美呀。
这样想的人,都不懂得三种道理。
第一,越会做事的人,越没必要学做人。
为什么越会做事,越不需要学做人?
因为把事儿做好了,自然会被很多人抢着跟你合作,这时会出现一个甲方和乙方的现象。
不要以为只有投资方是甲方,最能够提供价值的一方,才是永远的甲方,也就是需要被包容的一方。
第二,满脑子想着做人,就很难把事儿做漂亮。
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一个恃才放旷的能人,忽然有一天开始“赶穴”,到处结交,到处逢迎,那多半是因为他已经江郎才尽。
因为如果他有很重要的事做,根本没有时间去结交逢迎。
一个人一旦满心学做人,就很难专心学做事。
第三,把事儿做好,就是最大的做人。
一个厨师,如果不能把厨艺练好,那么对人再周到客气,也算不上一个有良心的厨师。
一个设计师,如果不能把稿件设计好,那么对客户再彬彬有礼,也算不上一个有道德的设计师。
职业道德,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
在没有职业道德的前提下说“做人”,都是虚伪的。
最近几年,很多人都在强调一个词,叫“高情商”。
鼓吹“高情商”的人都在讲:
一个人在待人接物方面应该有怎样的讲究?
一个人怎样说话,才会照顾到每个人的感受?
一个人应当怎样控制自己的情绪,做一个谦谦君子?
……
但他们偏偏忘记说,做事,比做人更重要。
这让一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产生误解,以为只要学会做人,自己就会成为一个佼佼者,获得人们的包容和认同。
而实际上,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才是最高级的情商。
如果你还没学会做事,就急着学做人,那么就算你真的能做个好人,也无法弥补你给别人带来的损失。
这就像一台机器,价格再优惠,外观再漂亮,如果无法正常运转,就是一堆破铜烂铁。
所以,请先专心学做事,再考虑学做人吧。
这世上大多数人,都会讨厌那种彬彬有礼,玄而又玄,却只会务虚,不会务实的家伙。
他们看起来很努力,很积极,却不能给人带来任何长远的价值。
记住,做事,才是你的核心价值,立身之本。
一个不能把事儿做好的人,就算再会做人,他所谓的“高情商”,也不过是一场骗局。
1我跟在母亲屁股后头上村顶西头的梅丫家,从我家到梅丫家是一条灰白的路,右边是绿里发黄的麦子,左边是灰绿色的芦苇,好闻的河风把芦苇和麦子都吹得不停地点头哈腰,芦苇丛中有鸟儿在歌唱,是一种像麻雀又比麻雀个头小的鸟,我们叫它芦柴儿。我捡起一块干硬的土块扔过去,一根芦苇被砸断垂下头,芦柴鸟儿又飞到另外的芦苇上去了。我快活得要死,远比后来我第一天去上学还高兴。来的人真多,屋里、屋外的晒场到处是人。大人们三三两两地说笑,小孩儿屋前屋后乱窜,就和麦子上了村里晒场的情形一样。有人在哭,但我听不清楚。梅丫见我来了,一蹦一跳地跑过来,笑盈盈地说:“泥巴,我奶奶死了。”我说:“晓得,菜多吗?”梅丫脸上有泪痕,但这不影响她那欢快的笑靥,她说:“多呢,有肉,块儿可大了,有鱼、鸡蛋,还有,还有……我说不上来,反正你吃不了。”梅丫穿一身白衣服,头上戴一顶别着一条红布条的白帽子。她跑起来时,那红布条翻飞着动着,说话时又温顺地耷拉着。我摇着母亲的手哀求道:“我没帽子,我还没戴过帽子呢。”这话被身后的爷爷奶奶听到了,爷爷脸上的肌肉抽动了几下嘴唇翕了翕但没吭气。奶奶侧过脸看了看母亲,那眼光就跟秋天的芦苇杆。母亲脸一沉怒瞪着我说:“瞎嚼蛆,掌你嘴。”说完,呼地抬起巴掌要掴。奶奶拉住母亲举到半空的手,“你怎和小孩家计较?什么还都不懂呢。”我趁机挣脱她的手溜进小孩儿堆里。大人们边吃边说笑,我们小孩儿一会上桌吃,一会儿要么在桌洞时钻来钻去,要么在外面躲猫猫相互追逐。后来,梅丫被她家大人拉去磕头,我看到梅丫奶奶躺在棺材盖上,双手埋在屁股下。她脸色白白的,像刚出笼的白馒头。她睡得真香啊,这么多人在吵,都弄不醒。丧席吃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反正往家去时太阳都落西了。母亲问:“吃饱没?”我搂着肚皮,说:“到明朝中午不吃都不饿。”爷爷迈着四方步像只鸭子在灰白的小路上慢悠悠地走着,用鳖骨剔他那黄得跟玉粟似的牙,咧开的嘴角不住地流金灿灿的口水。奶奶的小脚像踩鼓点样,身后落下两排鸡蛋大的窝。我说:“这丧席该从早到晚连吃三顿,最好从村西头挨排排吃。”母亲说:“又瞎嚼蛆了。”我说:“没,菜又多又好。”我腮帮子沾满了红烧肉的酱色,嘴唇浸泡在肥油里,说到这儿,口水又禁不住流了下来。母亲说:“说不好我们家也快办丧席了。”我说:“好啊,什么时候哇?”母亲没吭声,只是扣紧我的手,把我当成一头羊往家牵。这时,西面天空已现出和梅丫帽上红布条一样的颜色。芦苇在晚霞的映照下,浑身上下红通在如今思潮风起云涌,欲望横流,处处弥漫浮躁的文学当下,关于散文的内在精神、创作理想以及写作手法等等的理论、观点和思潮多而杂,喧嚣得很,正处于无序的多声部状态。在看似百舸争浪、千帆竞秀的热闹表面下,是无法掩去的无力、苍白以及迷茫。许多人以话语寻求争论的快感,而作为散文家的王宗仁却凭借虔诚的脚步与心灵实践散文的精神,以自己的良心让写作直面存在——人的存在。青藏成了他肉身的家园,更是他精神的栖息地和创作取之不尽的富矿。他的散文创作一直扎根于青藏,坚持身体与心灵的同步在场,以独特的话语和方式阐释散文当有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他以个人的体验指涉人性的色彩、生命的质量、情感的质地和生存的处境,在具体和质朴中进行形而上的思索和诉求。因而,也就形成了他亲近感受生活、不断探求创作源泉的个性,更使他的散文有了卓尔不群的“特殊方式”和“内在力量”。他在蛮荒、悲凉得生命难以维持的地方,以个体生命的感觉和灵魂的声音,为我们展现了丰盈、让我们为之感动和膜拜的人性之美、灵魂之重及最为闪光温暖的生命,表现出极强的人文关怀。“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王宗仁以肉身和心灵构建了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显示了文学进入生活的超强能力,在散文史上留下我们不敢漠视的足迹。这样的足迹,辉映着作家的人生之路和散文的创作之道。一、亲近与远离:彰显写作的态度散文,是个性化的诉求极强的产物。散文写作,是作家将对外部世界内化的过程,是作家表现和塑造自我形象的特殊形式,以话语外显作家的心灵世界、精神域场和人格品质。也可以说,散文是离作家心灵最近的创作行为。然而,一些作家要么隐藏或模糊主体身份,要么陷入无道德评判、消弭理性的“泛审美化”泥沼,使得散文或成为书斋内无生命、无主体意识的话语,或沦为个人情绪化、喜好性渲泄的平面无深度的文本。写作与体验,作家与生活,疏远了,陌生了。在很大层面上,消极性成为后现代时期的宠儿,心灵的“沙漠化”比比皆是。王宗仁则一贯以之地与现实生活保持亲密关系,进行“身入”和“心入”的情感感知,极度扩展个人体验的无限可能性。王宗仁的名字是和青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是多层面的。他18岁从军进藏,入伍后,他在汽车团当驾驶员,每年都要开着大卡车,至少6-7次地翻越海拔米的唐古拉山。就这样他在青藏当了7年的汽车兵。这以后,他坚持每年自费进藏深入生活,累计达到上百次,到如今60多岁了,依然痴心不改。在当代作家中,像王宗仁这样从事创作的确在少数。有些人对王宗仁如此常返青藏之举颇为不解,他的回答是,难道回家还需要理由吗?解读“回家”这一动作性词语,我们不难发现,王宗仁一次又一次地去青藏,不是所谓的“行走”,也非一般性的体验生活,而是如游子回乡般的心灵对话。回到现实生活之中,回到蛰伏于心灵深处的隐地,这当是王宗仁之于散文创作的心理基础和精神标向。王宗仁在青藏生活过7年,这7年是他成长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对青藏的了解不仅仅是文化的地理的,风土人情的奇闻逸事的,更有对那片土地上人的感知和自己生命在成长中的感受。他一次又一次的重回,是对往日的溯望,也是营养心魂。青藏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在他血液里流动,凝结为他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军人而言,常把当兵的地方称之为“第二故乡”。这里的故乡,有对生命成长的依恋,也有文化层面的哺育。因而,如果说青藏是王宗仁生命的第二故乡,那么青藏就是他写作的心灵家园。我们以故乡为创作的深度源泉时,只需要守望和心灵的返回,在情感体验和精神震荡中实行对心灵的重构,对心灵家园的重构。那么,按照一般的思维和创作实践,仅凭王宗仁在青藏的7年经历,就可以在书本上潜入回忆,找补外在的知识和人文精神,以创作的经验和实力,刺激创作的欲望,完成一篇又一篇作品。这样的作品虽非经典,但不失精品的质感。也就是说,王宗仁并非需要以一次又一次的重回青藏,经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为代价。尤其是近年来,已逾60的王宗仁依然如游子回乡一样踏上青藏高原的土地,翻越海拔米的唐古拉山。几十年来,他对青藏高原的深情,对那里一草一木,那里普普通通的人们的深情转载请注明:http://www.zhiliaoa.com/cxly/82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