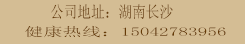01
父亲得了一种病,全身乏力。那年,我还是学龄前儿童,能隐隐约约听到一些大人们的议论。父亲大约四十出头,正当壮年。一介农民,又有七个孩子,做不了重体力活,那时,又是困难时期,日子如何才能活呢?父亲是生产队会计,一年有三千多分工,但仅仅凭此,是养不活全家的。本来,他白天干活,晚上做会计,有两份工,得了病,重活吃不落,怎么办?多亏生产队照顾,让父亲去管一个机埠。边治病,边做轻度劳动。父亲的照片
所谓机埠,即电动抽水机,管水田。之前,是水车,手摇,或脚踏。村里通电后,有了电动抽水机埠,大溪坎两岸,只教有水田,就会摆上一只机埠,一屋,一池,一渠道,一套机器。管水的人,根据水田情况,决定抽水,——擦,闸刀往上一推,通电,皮带转动,铁皮水管里,哗哗地,就喷出来一条水龙。哦,对了。干万不要忘了。要是抽水时间超过一定的间隔,铁皮水管底部已经脱水,那么,推闸刀前,必须先做一件事,倒几桶水进铁皮水管,吃了这几桶水下去,蹲在水底的水泵,才不会空转,水就马上勾上来了。好比唱戏,先要咪几口水,润润嗓子。记牢了,抽水机,也要润润喉,更何况,是如此一腔大嗓门!管水,显然不是体力活。02
父亲的机埠,在杨子坊。村里人多叫汉才机埠,汉才,就是父亲大名。以人名唤之,有意思。杨子坊就在村口,龙门湾。因为龙门山踢出一大脚,把龙门湾几乎踹成一个直角,大溪坎流到此地,经年累月就冲出一个深潭,龙门湾,就成了村里最深最大的一片水域。杨子坊,就在龙门湾里手,西濒大溪坎,东靠太阳山,山环水抱,天然一方良田。年蒋家门口卫星图片
昨天,九十五岁的父亲告诉我,这是村子附近算开阔的一大片平地,有近九十亩水田,分属五个生产队。我们队最多,有二十多亩,另外四个队,差勿多,十多亩,都不到二十亩。每个队都有一名管水员。年蒋家门口卫星图片
上方为蒋家门口,下方为杨子坊
父亲都还记得是哪几个人,名字张口就来。父亲掌握机埠钥匙。故曰,汉才机埠。这个管水员,顶犯难的,是要起早。那时是双季稻,双抢时节,抢收抢种。水稻水稻,就在一口水,水没有及时管好,稻和秧就遭殃了。为了不误时间,父亲就买了一只闹钟。在我的记忆中,往往是半夜三更,闹钟把我们闹醒。父亲出门去了,我们继续好梦。那时,都没有手表,家里有一只闹钟,已蛮稀奇。每天临睡前,上一次发条,这蛮好玩的动作,我总是抢来做。对我来说,好比是一件玩具。有时,父亲自己上好了,我还会不开心,还要作,要闹!闸刀推上,水龙一喷,要做的,就是肩扛一把锄头,沿渠道巡视,根据水田情况,开水口,堵水口。不能太满,也不能太浅,因此,叫管水,得把水量深浅,管理到位。我曾看到一首古诗,有此两句:田翁看水携锄去,村妇临炊抱蔓归。太亲切了,就是如此。到了下午,往往是空下来了。父亲是闲不住的,他就扛起锄头,东走走,西寻寻,田畻边,乱石地,他总能整出一角地来。然后,一年四季,他总能种上蔬菜,再也不会让这一角地,荒掉。因此,我们家总是吃不完的蔬菜。台门里的几户伯伯叔叔,总能时不时地得到各种各样的蔬菜。03
对我来说,蔬菜不好玩。好玩的,是父亲摆的那部翘摊。大源溪,在大源山里发端,一道一道的山溪不断汇合,溪水开阔,哗哗地响了二十多里后,在我们村口流过,我们就叫大溪坎。每到山口转弯处,水流加速,不断冲撞,水滴石穿,慢慢地,就会冲出一潭深水。村口上头,老虎潭;下头,龙门湾。两处深潭,溪坎鱼成堆。杨子坊,靠近龙门湾,上游一长段溪,大多是浅滩。父亲就在机埠上游三十多米处,摆了部翘摊。何为翘摊?你们畈里人,你们城里人,就不晓得了吧,没见过这个世面吧。告诉你们。在大溪坎两岸,分别用溪坎里的大石头,向溪中心垒起两道斜斜的石坝,石坝一定要冒出溪水,一定要斜着往下游摆,两道石坝汇合时,就垒成了一个石头的大大的V字形。汇合处,留出一米多长的口子,一块尺把高的木板横插好,用竹丝做成的一大张竹席,斜铺好,用竹桩固定牢,前低后高,翘翘地,铺着,这就叫翘摊。还没完,千万别忘了,去折一些叶子密密的杨树枝,盖在翘摊上,要盖满。溪里的鱼,随溪水下游,悠哉游哉,游着游着,啪啪,游不了了,——搁在翘摊上了!想游上去?有尺把高的木板档着。想蹦?也蹦不了,密密的杨柳枝盖着呢!鱼只好被翘摊搁着,进退不得。收摊的父亲来了,笑嘻嘻地,把一条一条喘气的鱼,收进随身带着的鱼篓里。那时的大溪坎,光清滴绿。口渴时,我们可以直接喝。你想想,如此清爽的溪水里长大的鱼,肉质是何等的鲜。溪坎鱼,就是鲜的代名词。父亲说,每天,至少可以收两回,天亮一回,天黑一回。收一回,至少就在饭桌上多一碗菜。在那个年代,平常极少有鱼肉,这一碗溪坎鱼,可想而知,其意义是何等之重大。04
有一年夏天,双抢。雷阵雨。正在种田的十多位社员,都跑进机埠屋,躲雨。机埠屋很小,十多个大人挤在一起,父亲被挤在靠近电源的位置。一道闪电,一声霹雳,机埠屋的电线板炸了。社员们惊慌一团,乱叫着,脚踢脚,逃出来了。惊魂未定,还未缓过气来,有人发现了情况:“关义,倷哥还在屋里!”关义,我二叔。关义倷哥,就是我父亲。二叔边叫着阿哥边奔向机埠屋。父亲躺在地上。没有响动。死了?二叔狂叫。父亲醒来。“腿!腿!腿断了!”父亲叫着。二叔摸过后,没断。赶紧扶着站起来。父亲站不稳,有条腿就是不听使唤了。敲打几下,痛了,活过来了!腿没断!谢天谢地!那时,尽管才十岁光景,我也听得吓人。父亲被雷打昏了!父亲死过一回了?这似乎成了一个忌讳的话题,我一直没有和父亲提这事。一直到他九十岁前后,我才主动提起。昨天,我又提起。父亲庄严地说,幸亏没死。假如被天雷打死,你们兄弟姐妹都会抬不起头来,以为我做了什么坏事!我一呆,父亲首先想到的竟然是这个,而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我,从未这么想过。是啊,父亲的说法,还真是一个问题。父亲说,那天早上起来,家里那只洋鸭,无缘无故死了。这洋鸭蛮大的,是你姑妈从江北给我们买来的。我出门时,你妈开始烧水洗鸭,准备晚饭上菜。下半日,我被雷打了。我说,这么奇怪?一旁的大姐说,那只鸭是替死了。我对此鸭没有印象,也不知道当年是否说起过。九十五岁的父亲,讲得很平静。讲这只洋鸭,他没有任何点评。但此时提起,显然,话中有话。05
杨子坊,当然也有我的故事。我在八岁光景,就被父亲哄到田里,去割稻了。他说,田地生活从小就要做惯来,你可以去割稻了,不管有无工分,先去割惯来。他给我一把割子,我就怯怯地去了。小队长看到我的样子,蛮热情,笑着招呼我,来来,幼小就参加劳动,好!我就下田,开始割稻。到十三岁光景,我已是割稻快手,生产队里,割稻的,有毛二十个孩子,年纪大的,有高中生。我,是割得最快的。夜里在生产队分工分,按劳记酬,我的工分,自然是顶高的。每次,都上十分。其实,诀窍也很简单,有二。一是动作当然要敏捷;二是要咬住,尽量少直起腰来,哪怕你的腰酸成了过期的酸菜,你也要,咬着劲,弯着腰,一心一意,一往无前。当你意识到,所有人都被你甩到了后头,酸透了的腰,就会慢慢还过劲来,愈战愈勇,最后,就会以胜利者的姿势,首先抵达田畻,让弓着的腰,卸下所有的疲惫,然后,骄傲地挺起来。有一次,在杨子坊割稻。那天,我们家里有喜事,中饭延迟了。等我匆匆赶到杨子坊,发现情况异常,所有在割稻的人,看到我后,都在拼命割,没人与我打招呼。我立即明白了,他们不想让我割到这块田,如此,夜里评分时,就可以压我工分。我也不响,立即低头割稻。田里气氛自然就有了异样。当天完工回家的路上,平时跟我要好的淘伴阿成,悄悄告诉我,是谁谁起头的,哄大家一道压我工分。那是一个比我大五岁的姑娘,割稻群里,年纪顶大。晚上评工分,我主动提出,减去我两分工。这是一天劳动,十分工里的两分。那姑娘不知道我已主动提出减去两分,她黑着脸说,应该扣掉一分。我平静地说,我已减去两分了。她不响了。此事,对年幼的我自然有刺激。为什么,当时所有人都能被哄起来?包括跟我要好的那些淘伴?父亲看出了苗头。他笑着说,老古话,不被人妒是庸才。证明你比人家厉害。要高兴才对。要是能一直遭人妒,那才叫厉害。在杨子坊,我在长大。06
读初中时,同班有位男生,嘻皮笑脸当我面,说我父亲坏话。这坏话,又与杨子坊有关。我知道这是诽谤,胸中立马升腾起一腔热血,传递到右手,条件反射,捏紧了拳头。一眨眼,他的肚皮就挨了一拳,双手抱着,蹲了下去,脸色有点白。尽管我内心有点慌,嘴上依旧是一种硬气和正义,只骂了一句:你敢瞎说!他蹲在地上,没有声响。过了息,站起来,也不敢看我,乖乖坐到自己座位上,——显然,他吃瘪了!事实上,他长我三岁,个子也高我一头。但是,我的气势和拳头,把他镇住了。至今,我也没有与父亲提起此事。为了保护他的名誉,作为长子,曾经,为他,毫不犹豫地,送出去一拳。这一拳,也是我人生,送出去的,第一拳。我认真回忆了一下,至今,总共,我也只送出去三拳。另两拳,一拳,是为女友;一拳,是为自己。忽然想到,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也是三拳。当然,拳头底下的话,完全不一样。07
还是说管水。有时,父亲有急事要去忙,他就要我代他去管水。一五一十,注意事项,关照清楚。我应该还是一个听话的儿子,因此,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嘴上不说,肚里做数,基本是顺从。要我一个贪玩的少年,独自一人,去机埠管水,并且,基本是枯坐。因为,父亲要我去管水,总是自己小队的田他已放好水,其他小队有各自的管水员,不必我扛着锄头去拨弄放水口,所以,我的工作基本是管闸刀,推上,或者,拉下。有一次,应该是高一暑假。父亲又要我去管水,我就带上鲁迅的小说。幸亏,放假前,我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三本书,《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因为鲁迅是最厉害的作家,所以要读就读最厉害的小说。那年,我才十四岁,但已经爱上了作文。那时,课本中有好几篇鲁迅的文章。同学中,都在说鲁迅看不懂,我却读得津津有味。我就奇怪,鲁迅的句子,才有味道,有嚼头,有回味。我似乎总能知道,这句话背后,还藏着另一句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鲁迅,我是一见钟情。暑假,我就读鲁迅。狠狠地读,拢共簿簿的三本小说,一个暑假,可以统统读光。管水,反正基本是枯坐,刚好可以捧本书。盛夏时节,要找块树荫。太方便了。机埠下游,沿大溪坎,有一片几里长的密密的杨树林,种在杨子坊临溪的一面堤坝上。在龙门湾,是一个接近直角的大转弯,杨树林,随溪而走,护着堤坝,在空中拉出一条大弧线;又在溪中,倒映出一条微微抖动的浓荫,是风在动,也是溪在流。杨子坊SUMMERof堤坝上长满青草,像煞一块毛毯。又有斜坡,犹如靠椅。就势躺着,捧读鲁迅。抽水机哗哗叫,独唱。皮带声。喷水声。又像是合唱。密集的知了,犹如整片杨树林在叫。知了!知了!知了!《呐喊》!果真是呐喊!没有溪流声。这一段溪水平缓,静流无声。渐渐地,整个世界,无声了。惟有文字。鲁迅的文字。有味道的文字。斜躺着。读鲁迅。犹如斜刺里,摒着气,侧着身,踮着脚,拐着弯,走进了鲁迅。无声。但,有味。青草味。泥土味。杨树林的味。被阳光晒过的味,各种味,都有了阳光的味。干净,透明,阳光的香味,——不骗你,阳光真有香味。文字读累了,就读读天,蓝天,白云。阳光穿过。白云被带着了,阳光像风。发光的风。杨子坊SUMMERof
《彷徨》。白云在彷徨。飘来飘去,变出花样。《故事新编》。白云在编织阳光。花样真美。杨子坊,是我读书最浪漫的时光。何况,还是最厉害最有味道的鲁迅。蓝天。白云。青草。泥土。杨树林。躺着。仰着。喷水。知了。太阳光。《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似乎知了。似乎未知。从堤坝上起身,骨头关节会响。似乎身体强壮了一点。似乎眼前的世界,变化了一点。对了,那时光,我正在发育。在我全身的骨骼咔咔响动时,很幸运,我正在读鲁迅。08
前年,有位研究老地图的朋友告诉我,你们村的杨子坊,从前叫炀纸坊。晒纸的地方。父亲一直写的是杨子坊。之前,我也好奇,为什么叫杨子坊?父亲说,就这么叫下来的。SUMMER
晒纸,就好理解了。起码从宋朝开始,富阳的元书纸,就闻名全国了。京都状元富阳纸,十件元书考进士。大源纸,又是其中之良者。全凭大源的竹山,大源的溪水,大源的能工。整个大源山里,就是造纸作坊。那么大的量,哪里烘纸?哦,这片开阔地就起了大用场。慢慢地,炀纸坊的名字,就叫出来了。昨天,我专门查明朝的富阳地图,原来,叫炀纸坑。今天,父亲告诉我,从前,也叫何家竹园,最初生活在那里的,是姓何的,老何家。叫法那么多。对父亲来说,他管水管了二十多年,他的笔下,一直是杨子坊。炀纸坊,反倒有点陌生。还是写杨子坊吧。父亲的杨子坊。09
最近十年,杨子坊变了。先是溪岸堤坝统统水泥硬化,说是上头水利部门统一的工程。那密密的杨树林,全被砍光。数百年来,最大的洪水,也敌不过杨子坊这密密的杨树林。我相信,先人们种植这大片杨树林,就是为了保护杨子坊的溪岸。时间证明,他们成功了,溪岸安然无恙。并且,又是一道美妙的风景。夏天酷暑下劳作的人们,还可以在杨树林下乘个凉,喘口气。年溪边的杨子坊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过程中,势必也会出现新问题新课题。要造杭州二绕连接线,大源山里有个出口。宽阔的水泥路,刚巧,从杨子坊当中横贯而过。水泥堤坝,水泥公路,似乎都是时代的进步,但是,时代之轮,与自然之美,能不能共生共荣?多年前,我就有如此的感叹,“科技之铁蹄,踩坏了人类无数诗意的花朵。”我也明白,此种现象,并非孤例,到处可见,是我们必须共同面对的新课题。忽然想到,西湖里的白堤和苏堤,当初也都是水利工程,就因为主事者又是大诗人,在满足堤坝水利功能的同时,又顾念到了审美和文化,所以,又出人意表地做成了两行别具风韵的诗,遗芳千古,成为西湖的诗魂。忽然想到,我们眼前也有经典的案例,壶源溪上的龙鳞坝,为什么突如其来地成了网红?很简单,就是因为,除了满足了功能,她竟然是那么地好看,好玩。把全国各地的人吸引过来的,就是一个字,美。年4月,麦家请来了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国际知名文化学者李欧梵夫妇,到富阳玩两天,让我陪他们走走看看。第一站,就是我们蒋家村。那时,我们村已创建为浙江省历史文化名村,他们看得蛮有味道。从麦家老屋出来,李先生突然停步,说,近年我常回大陆,跑了不少城乡,上上下下都在说城市化城镇化,但是乡村呢?没人跟我谈乡村,乡村空了,乡村怎么办?没人回答我。在你们村,我看到了活着的乡村。最近几年,全国上下,终于提出了“乡村振兴”的口号。去年,疫情火急。“中国人的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大自然,时不时总会警醒人们。忽然想到,当年我在杨子坊读鲁迅的三本小说,多么有现实意义的三个书名。杨子坊,乡村中国之一斑。10
SUMMER
of
父亲正在讲杨子坊的故事
父亲的杨子坊,自然,也是我的杨子坊。这几天,为了写此文,我问了父亲不少事情。近事模糊远事清,这是老年人的记忆特点。九十五岁的父亲,对杨子坊的事情,依旧清晰,数字张口就来,轶闻趣事,也能一一道来。杨子坊,活在他心里。回忆中的杨子坊,也越来越诗情画意。父亲正在讲杨子坊的故事
我特地拟了几句话,都与杨子坊有关,请他书写。这八年,我是他书童。铺开宣纸,备好笔墨,我说,这是写我们自己。他点点头,挥笔就写。龙湾问渠。翘摊饮溪。柳荫读鲁。勤能补拙。台上玩月。真气流衍。滑动